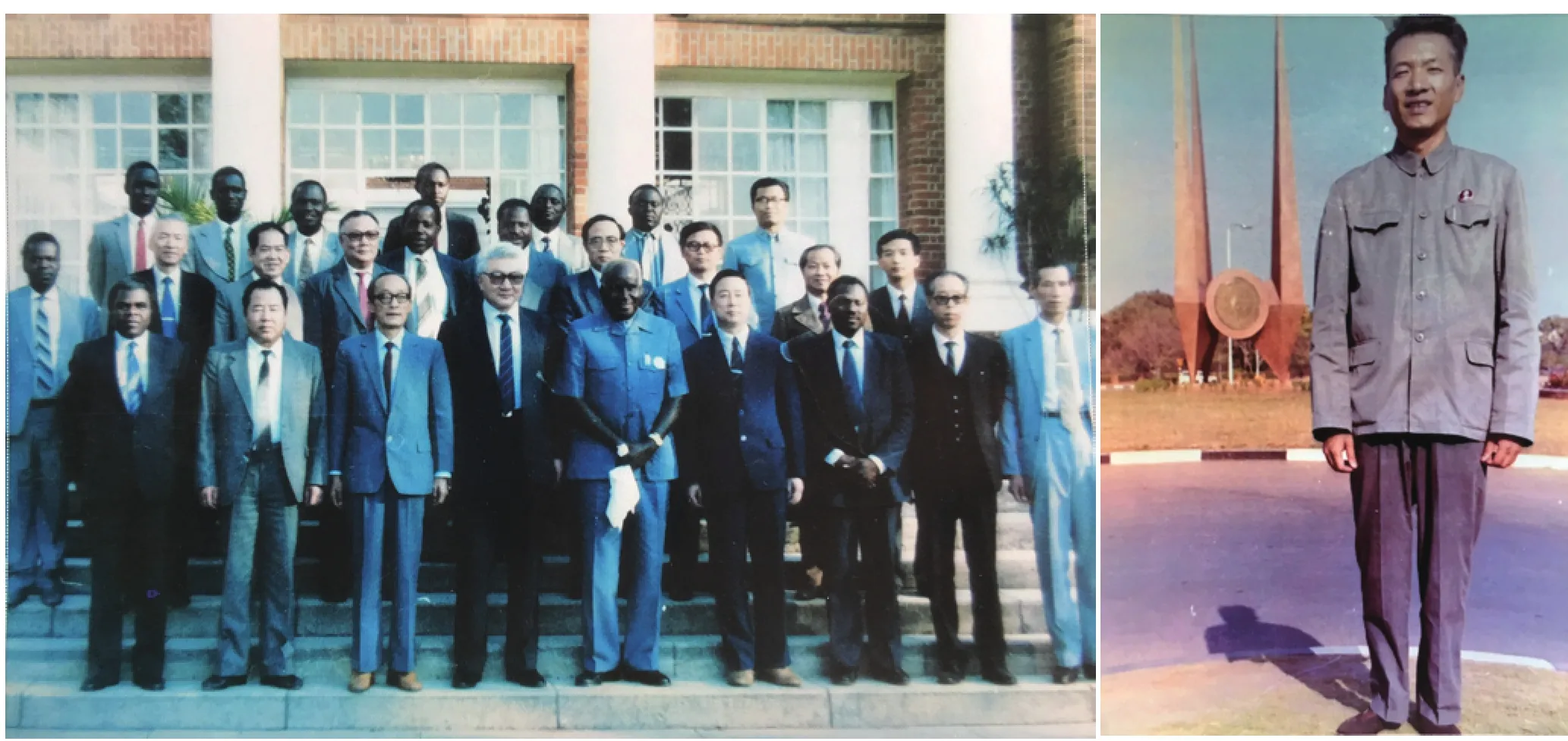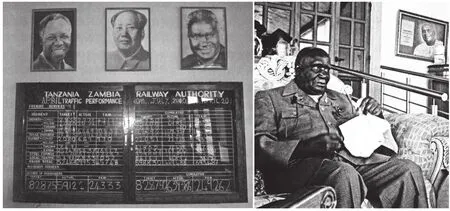王幼于
《浙大校友》1996 年下期摘登,1996年10月
我原名王勤增,1932年自宁波效实中学考入浙江大学化工系。1934年秋因病休学半年,1937年夏毕业。在求是桥畔度过了四年半。
1997年母校浙江大学百年大庆。我离开母校正好过了一个甲子。虽已是耄耋之年,记忆力还算不错。六十年前求是桥畔往事,历历在目。爰借浙大校友征文之机,略述数端,一抒怀旧之情。
一、忆师长
浙大化工系,是由李乔年(寿恒)师创办的国内第一个化工系。我得以亲承李师教诲,印象最深的是他亲自开的“杂志报告”课,要学生去图书馆阅读化工文献,把阅后收获写成文字材料,并每次指定几名学生在课堂当众作报告。这对培养学生查阅文献能力和学习自觉性十分有效。学生有了这种能力,可以终身受用。
我忝列李师门墙,毕业后原由李师推荐应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助研之聘,以“七七事变”发生,未能到职。抗战中虽一度在化工厂工作,然时间不长,主要是在中学、大学任教,解放后又转入出版界,从事科普工作,可以说用非所学,愧对乔年师。我从事出版工作,也忘不了李师当年在这方面培育之恩。李师的论文《柏尔氏纯煤热值分类法对中国煤的适用性研究》发表在1937年《浙江大学工程季刊》第2卷《化学工程》上,这期刊物就是在乔年师直接指导下由我做具体编辑工作的。
1992年4月,乔年师九十五华诞,我正好在杭州,去浙江工学院参加庆祝会,见到阔别半个多世纪的乔年师,虽因腿骨受伤行动不便,但看去精神矍铄。听了他在会上致词,专门讲了竺校长日记中提到他当年打麻将的事,说他听了竺校长委婉批评以后就不再打麻将,感谢竺校长对他的帮助教育。这段话讲得十分风趣,使我回忆起当年每年在化工系迎新大会上,乔年师总是讲一个孔夫子和耶稣对话的笑话,说是耶稣问孔夫子:“我们西方人吃饭时喜欢相互交谈,为什么你要大家‘食不言’呢?”孔夫子回答说:“因为你们西方是分食制,一人一份,我们东方是共食制,你吃饭时说话,菜就让别人吃完了。”在这次祝寿会上听了乔年师关于打麻将的这段讲话,觉得风趣不减当年。可是回味一下,他以如此高龄的长者身份,在祝寿会上却以揭己短作为话题,实在意味深长,不仅显示他坦诚磊落的精神,实际上是以自己的体会教育像我这样的晚辈,人不怕犯错误,重要的是知错能改。
化工系当年的教师中,潘承圻和吴锦铨两位也深受学生爱戴。潘师教无机分析,他除了课堂教学条理清晰之外,特别对分析实验抓得很紧,对每一个分析项目,给每一个学生各发一个分析样品。一班学生有几十个人(化学系学生也在化工系上课),他每次都亲自配几十份不同的样品,要求学生分析的结果和他自己所掌握的数据误差不超过百分之零点几。他的严格要求,培养了学生作精密分析的能力和干工作要一丝不苟的精神。他在教学上严肃认真,平日言谈中却和蔼可亲,说一口苏州话。当年潘师的音容笑貌,一直深印在我的脑海中。吴师教工业化学,循循善诱,一副慈眉善目,在学生中他以菩萨心肠闻名。吴师1936年离浙大去上海中国植物油料厂,我们1937年三四月间毕业旅行过上海参观这个厂,吴师亲自热情接待。吴师离校后,新来了程耀椿老师,教我们化工原理。1937年去上海南京北平(今北京)毕业旅行,就是由他带队的。他和学生同宿同行,还在北平便宜坊请大家吃了一顿烤鸭。解放后1952年,我在北京,曾在东安市场远隔十来米见到过他,可惜因人群拥挤,没有追上他。后来听乔年师说他当时可能在清华大学。
除了化工系的几位老师,还有化学系的陈嗣虞老师,教我们有机化学和有机分析,细心耐心指导我们做实验。他解放后在杭州大学,我曾写信向他问候。当年教过我们的老师中,印象较深的还有教微积分的朱叔麟老师和教画法几何的胡仁源老师,在当年算是学校中德高望重的两位老教师,当年全校正教授只有陈建功和苏步青两位,也只有三四十岁,朱、胡两师已经有五六十岁。教我们电机工程实验的孙潮洲老师,抗战中我在福建南平见过他,当时他处境很困难,贫病交迫,不久就听说他去世了。
我还要特别提到教我们二年级英文的一位老师倪夫人,原籍美国,是电机系一位副教授的夫人。她对学生要求很严,差不多每星期有一次发卷测验。有一次我己交卷,从讲台回到自己座位,坐在我后面的一位同学低声跟我说了一句话,我简单回答了一句。倪夫人当时就指责我们舞弊。卷子发回时,我的卷子上除了应得的九十几分之外,又把这个分数用两条杠划去,另外写上一个“0”。当时我觉得很冤屈。后来想想,这样的严厉处分还是对学生有好处的。
六十年前教过我的老师,现在大概都己作古。李乔年师最长寿,也已于1995年去世。对于培养过我的老师,我怀着深深的敬意写下这些一鳞半爪的回忆。
二、忆旧友
我1932年考入浙大时,效实中学同班同学还有七位。化工系有刘馥英大姊,她1936年毕业后去德国留学,在科研和教学工作上成就卓著,现在华东化工学院。电机系有许声潮(兴潮)兄,1936年也去德国留学,解放后在上海华东电力试验所,退休后去美国探亲。汪闻涛兄,解放后在南京江苏电力试验研究所,退休后仍在做有关本行的一些学术工作。机械系有韩文藻兄,毕业后曾留校任助教一年,后去铁道部,抗战中去美深造,解放后在铁道部武汉设计院退休。农学院有陈迟兄,抗战中曾去美国留学,后在亚洲开发银行工作,现在美国定居。他们都在本行工作中作出贡献。我遥祝他们晚年幸福!还有两位已经去世,一位是电机系的邵培梓兄,解放后他在北京供电所工作时我和他有来往,六十年代初他去新疆,后来听说在一次出差途中遭匪徒杀害。另一位是姚积尧兄,毕业后去航空署,解放时留在大陆,是起义人员,“文革”中惨遭迫害,以致半身不遂,八十年代初去世后才得平反。我对邵姚二兄怀着深切的悼念之情!
因为我一度休学,所以化工系中我和36、37 两届同学都一起上过课。36 届中除前面提到的刘馥英大姊,我还怀念姚玉林兄,他毕业后去南开大学应化研究所,后来考取庚款留美,我毕业后原来要去南开大学应化研究所,就是去补他的缺的。1992年我参加母校九十五年周年校庆典礼,见到北美同学会的代表,打听他知不知道姚玉林兄,他说姚兄仍在美国。韦人骝兄,毕业后去中国植物油料厂,我们去参观该厂时由他陪着我们。后来他在一次事故中右臂被皮带卷入机器,装了假肢。抗战中他在温州创办东南化工厂,当时因火柴厂需要的氯酸钾原料进口被封锁,他设厂用电解法制氯酸钾,供应火柴厂。1943年我应他之约去那个厂担任化学工程师,当时电机工程师是36届电机系的吴汪乾兄。1944年温州沦陷,厂匆促解散。韦兄后在巴基斯坦办企业,现在还在美国和巴基斯坦两处跑。36 届同学中有一位沈一鸣兄,毕业后不久在参观江阴炮台时被击伤去世,当时我还在校,闻讯觉得十分痛惜。吴汪乾兄解放后自淄博铝厂退休回太仓,曾为建设太仓电厂效力。
和我同届毕业的,陈东兄和我相交甚深。他也是1932 年进校的,因奔父丧休学一年。一年级和四年级我和他同住一室。四年级时我知道他和土木系的侯焕昭兄等同参加一个“团契”组织,实际上是假基督教宗教组织名义从事党的外围活动。抗战中他在福建筹建福建省企业公司下属的一所皮革厂,1940年我应他之约去那里任技师。后来因为省里经费支绌,厂一直只是试生产,我于1941 年冬离开那个厂。解放后1951年我曾在北京见过陈东兄,还相约同去看另一位同届同学陈国符兄。陈国符兄当时在北大化工系,院系调整后他去天津大学。他是留德学造纸的,对炼丹史很有研究,五十年代我在北京由中国化学会主办的一次中国化学史研讨会上听过他的一次报告。陈东兄后来在永利宁厂,五十年代我在报上见到报道他对煤的燃烧方面有研究成果,作出贡献,受到表彰。他后来任江苏省石油化工厅副厅长,退休后回到福州,健康情况不大好,我对他十分挂念。同届同学中吴珣兄毕业不久即因病去世,令人惋惜。另外在报上常见到邹元燨兄在治金方面作出贡献的报道,当选为学部委员,惜已在1987 年因病去世。在李寿恒文献室编的《桃李集》的“北美浙大化工系校友通讯录”中,我见到有张禄经、张格二兄的地址。
由于我毕业后正好发生抗战,大家行踪不定,所以除个别的以外,这届化工系同学大多失去联系。但是当年这些同窗的音容笑貌,我也还深印脑际。37 届化工系同学拍过一张毕业合影,我至今仍珍藏着。
除了化工系的同学,我还特别怀念一位电机系 36届的同学陈世昌兄。他毕业后留校任助教,我在念四年级,课后常去他的宿舍,有时聊天,有时打桥牌。解放后我先后在有关台湾校友和北美校友聚会的报道中见到过他的名字。大概现在也在美国。
三、忆学运
1935 年12月,北平发生“一二.九运动”,继16 日北平学生和市民第二次上街游行之后,杭州学生首先响应,也在市内举行示威游行。记得当时我的中学同学冯宾符兄(解放后任《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在上海参加进步刊物《大众生活》的编辑工作,来信要有关杭州学运情况。韩文藻兄为之写了一篇报道杭州学生游行情况的文章,我搞到几张杭州学生游行的照片,发表在《大众生活》上。
接着浙大学生会还策划全校学生去南京请愿。大约在12 月下旬的一天,决定全校学生一早去杭州城站坐火车去南京。那时我没有在学校住宿,为了能一早参加这一活动,头天晚上睡在电机系36 届同学曹寅亮兄床上,他已先期作为先遣队去南京。那天半夜里,突然有人敲门,进来了浙江保安司令部的两个士兵,对着我的床叫我起来跟他们走。我问干什么,他们说你不是叫曹寅亮吗?我说不是,是住校外借睡在曹床上的,他们先是不信,后来别室的同学都被吵醒起来,证明我的确不是曹寅亮,那两个士兵就不理我走了。那天夜里凡是在学生会里比较活跃的同学,大多在所住的宿舍里被抓走。
当时全校同学义愤填膺,一声号召,都在工学院操场集合,决定仍按原计划去南京。可是这时学校大门己由保安司令部的士兵把守。有几位同学带领大家悄悄地走文理学院新盖教学大楼后面临庆春路的一道小门,出门快跑沿庆春路过庆春门转上铁道,直奔城站,几百个学生排队站在铁道上,有几位同学向城站要求发车。那时杭州的火车是从闸口开出的,城站没有车,站里不肯发车。我们在铁道上从早上五点多站到大约十一点,有一位农学院的同学叫施尔谊(解放后曾任上海人大常委会主任,改名施平),原来也是学生会活跃分子,我们以为他大概已被抓走,他却隐蔽下来,这时站出来向大家讲话。原来这次出庆春门到城站的活动主要是由他指挥的。他向大家提出,“这次同学被抓,保安司令部按着宿舍抓人,一定是学校提了‘黑名单’。我们和车站多次交涉,车站不肯发车。现在我们己和学校当局交涉,和保安司令部交涉,要他们把被抓的学生放出来,否则我们就坚持在这里站下去。”大约又过了一小时,学校派秘书长来当众宜布,被抓学生己经放出,大家才离开城站走回学校。
这一次去南京请愿没有成功。回校以后,全体学生仍集合开会,除决定继续响应全国各地的学生运动,通电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停止内战实现抗日,还一致决定在校内掀起倒郭倒李运动。当时的校长郭任远,到任后就对学生实行军事管理,控制学生思想和活动,早已引起多数师生的不满。农学院院长李德毅执行郭的指示最卖力,也遭到农学院师生的反对。于是以这次向浙江保安司令部提学生“黑名单”为爆发点,发生驱郭驱李运动,罢课请愿。到1936年1 月,蒋介石曾到浙大召集学生讲话,学生也不妥协。这个学期没有大考就放寒假。后来郭李被迫辞职。
1936年4月,教育部任命竺可桢氏来长浙大,学潮才算告一段落。竺校长来浙大后,一变郭任远当年和学生对立的状态,以学者的风度治校,全校出现了祥和团结的气氛。
四、忆求是
1937年6月,在竺校长主持下举行了毕业典礼,我就离开了求是桥,回到宁波老家,准备 7月底去天津。“七七事变”发生,天津邻近战场,我于7月中旬又到母校找李乔年师,乔年师要我等一等再说。这是我在抗战前最后一次告别求是桥。
我在求是桥畔度过了四年半,对当年学校景象至今还大致记得。工学院仁义礼智信五斋印象最深,这是学生宿舍楼。北边一带是木工场、铸工场、铁工场、金工场,化工、电工、土木、机械、水利等实验室,化学分析实验室,南边一带是办公室、图书馆,中间有阶梯教室,后面是大操场。工学院出大门两边是小河,对面是一带小山。向南绕过小山,有一道门通浙江省立图书馆,向北过求是桥是文理学院大门。过桥东边后来新建了体育馆。文理学院里面主要建筑是郭任远长校时新建的教学楼,可是建成不久中间就有了对裂缝。我们一年级时上课有时在文理学院西边一带的平房教室里,有的课在工学院阶梯教室里上。新教学楼建成后就在教学楼里上课。化工系在刀茅巷,上有机化学课和做实验要到刀茅巷去。另外在校门外大学路上有一个宿舍大院,我们一年级时的宿舍就在这个大院里。
抗战胜利后,浙大回迁杭州,后来迁到新址。六十年代初,我出差杭州,曾去大学路访旧。到了原浙大校门口,印象中挂上了一个工厂的牌子,不让进,只好在浙江图书馆和附近转悠了一圈。以后一直到 1992年,我参加母校九十五周年校庆,又去大学路,原来浙大校门己经敞开,口上好像钉了一块“老浙大弄”的牌子。进了校门,已经面目全非。北面原来文理学院的那一带大概是一所工厂,原来的小山不见了,小河不见了,求是桥当然也没有了,原来小山的位置也是一座工厂,原来求是桥的地方有一个居委会。估计原来工学院的位置,找了半天才找到了进去的门,终于在里面找到一所破旧的二层楼房,看去当是当年五斋之一,但不知是哪一斋。闯进楼门,在楼下楼上过道走了一遍,在楼上找到一间屋子开着门,进去一问,说是一个防疫站,说这所房子是老浙大剩下来的唯一一所,不久也要拆去了。我在这所楼房前照了一张相,为我和求是桥的最后告别留一个纪念。
(1996年6月)